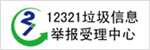朱丹溪

朱丹溪字彦修,名震亨,因家乡有条美丽的小溪叫丹溪,死后,人们尊称他为丹溪翁。由于他医术高明,治病往往一帖药就见效,故人们又称他为“朱一帖”、“朱半仙”。婺州义乌(今浙江义乌县)人,生于至元十八年(公元一二八一年),卒于至正十八年(公元一三五八年)。
在他小时候,读书能过目成诵,日记千言,言章词赋,一挥即成。,听说著名理学家许文懿在东阳八华山中讲学,专门传授朱熹的理学,他对许文懿讲授那套理学非常崇拜,听了,“自悔昔之沉冥颠齐,汗下如雨。”他“每宵挟册,坐至四鼓,潜验默察,必欲见诸实践。”这样,他坚持学了几年,日有所悟,学业大进,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“东南大儒”。
在他三十岁的时候,老母患严重的胃病。他心情焦急,请了许多医生治疗都治不好。原来这些医生,大都医术粗劣,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,盲目搬用《局方》。开的药大同小异,吃下去一点效果也没有。这时,他深深体会到:“医者,儒家格物致知一事,养亲不可缺”(《丹溪心法》序)。于是他立志学医,日夜攻读《素问》。以前,他也曾读过《素问》,觉得“词简而义深,去古渐远,衍文错简”,然后“茫若望洋,淡如嚼蜡”。这次他又取《素问》研读,经过三年的钻研,“似有所得”。又经过两年的精心治疗,母亲的病终于被他治好了。治好母亲的病,本来是件可喜可庆之事,然而却因此勾起他追念自己的孩子患了内伤,伯父患了瞀闷,叔父鼻衄,弟弟由于腿痛,妻子因为积疾,都一一死在庸医之手。回忆起这一切,他“心胆摧裂,痛不可追”。后来,他的老师许文懿也患了重病。一天,他对丹溪说:“我卧病已久,非精通医术的人不能救活,你聪明灵活,能不能改行学医呢?”朱丹溪慨然说:“我能精通一门医术,也有利于仁民爱物。虽然不当官,也象当官呀。”于是他抛弃一向所习的“举子业”,一心扑在医学研究上。
当时,社会上盛行南宋官方制定的《大观二百九十七方》,朱丹溪开始下苦功研究,手抄一册,“昼夜而习”。后来,他却产生了怀疑,认为“操古方以治今病,其势不能以尽合。苟将起度量,立规矩,称权衡,必也《素(素问)》《难(难经)》诸经乎!”(戴良《丹溪翁传》)。他还攻读张子和著作,拿它与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比较,发现“其书之所言,与《内经》、仲景之意若是不同。”究竟应当怎样解决前人的古方和今病的矛盾?怎样认识张子和汗、吐、下三法?怎样处理攻补的关系?朱丹溪决定离开故乡,到外地去访师问道,以求印证。
朱丹溪出游,几年间,渡浙江,走吴中、出宛陵,抵南徐,达建业,真是“负笈寻师,不远千里”。公元一三二二年,他辗转来到武林(今杭州),才打听到这里有个罗知悌,医术高明,有真才实学,便打定主意,拜他为师。
罗知悌,字子敬,世称太无先生,刘完素的再传弟子,在朝做过御医,不仅通晓刘完素之学,而且旁及李东垣、张子和两家学说。他在杭州名气很大,也很骄傲,保守,不肯轻易把医术传授给别人。
朱丹溪到了罗家门口,拱手立在一起,待罗医生出来接见。罗医生以为他来看病,热情地把他接到家里。但一经诉说拜师学医的来意,罗知悌就敛起笑容,叱骂他,把他赶出门。朱丹溪“蒙叱骂者五七次”,但不灰心,“志益坚,日拱立于其门,大风雨不易”,如此,“趑趄三阅月”。有人悄悄告诉罗知悌,来人是许文懿的学生,是东南一位有学问的人。这样冷落人家,恐怕会引起非议。罗知悌听后有些动心。一天,下着瓢泼大雨,罗知悌推开大门,见到朱丹溪在雨地里拱手而立。罗知悌深深被感动,马上“修容见之”。从此朱丹溪就成了他唯一的弟子。这时,朱丹溪已经四十四岁了。
朱丹溪很尊重老师,对老师的一言一行都细心观察领会,学习上有疑问就请教老师。罗知悌有这样一个得意门生也非常高兴,“一见如故交”,耐心地讲解刘完素、张子和、李东垣的书,阐述这三家的主要论点,指出他们学说渊源在于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。他说:“学医之要,必本于《素问》、《难经》,而湿热相火,为病最多,人罕有知其秘者。兼之张仲景的书,详于外感;东垣之书,详于内伤,必两尽之,治疾无怕憾。”朱丹溪听了,“夙疑为之释然”。在老师的指导下,朱丹溪认真研究了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本经》等医学经典著作,对刘完素、张子和、李东垣的著作也进行认真的研究,在医学理论有了很大的提高。他认识到“医之为书,非《素问》无以立论,非《本草》无以立方”(《格致余论》序)。当时庸医不谈这些医经,盲目搬用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(简称《局方》),墨守成规治病,当然不会取得良效。他细心观察罗知悌诊病,发现跟《局方》派完全不同。每天有人在床上,根据脉状,口授“用某药治某病,以某药监某药,以某药为引经”。一年半过去了,不见他搬用《局方》,但药到病除,疗效很好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罗知悌告诉他:“用古方,治今病,正如拆旧屋凑新屋,其材木非一,不再经匠民之手,其何乎用”(《格致余论·张子和攻击注论》)?经老师一指点,他终于想明白了:《局方》不是不能用,而是要根据病人体质、发病原因的不同,经过适当调整、补充或删改,才能取得疗效。用药治病,最要紧的是对症下药。如果不问病情,照搬《局方》,食古不化,那就是刻舟求剑,按图案骥,“冀有偶然中病,难矣!”
朱丹溪在罗知悌门下,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,勤问多思,终于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,从而学识渊博,医术精湛。他的老师许文懿非常高兴,说:“吾疾其遂瘳矣乎”(戴良《丹溪翁传》)!果然,在朱丹溪精心的治疗下,许文懿经过十几年治疗无效的“末病”终于治好了。数年之间,朱丹溪“声闻顿著”,名震远年,“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”。
尽管如此,朱丹溪并不自满,仍然虚怀若谷,访师问医。一次,浙中有位女子患“痨瘵”(肺病),骨瘦中柴,奄奄一息,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,眼看没救了。病家抱着一线希望来请朱丹溪。经过朱丹溪几天认真治疗,病情果然有了好转,只是两边脸平面上的红晕不退。朱丹溪也“技穷”,就对病家说:“现在要请吴县名医葛可久,用针灸治疗才会好。但这个人雄迈不羁,难得请来。我写一封信给你带去他就必来。”病家很高兴,就雇了一只小船去请葛可久。葛可久一见朱丹溪的信,即“不谢客行,亦不返舍”,就登舟来了。朱丹溪把那位女人的病情作了详细的介绍,并请葛可久诊视。葛可久认为病在胸肺,余邪未净,一定要用针刺两乳,便可愈。但在封建社会,男妇授受不亲,针乳就更难办了。葛可久想了一个办法,让病人穿着薄衣,即取针刺她的两乳。随之,病人脸上的红晕就消失了。这看来十分神妙,但有科学依据。因为“痨瘵”是干血痨,属瘀血。瘀血积于内,必形于外,表现脸颊红晕。据《灵枢经》说,胃足阳阴经脉是“主血所生病者”,经过乳内廉,用针刺两乳,即刺胃足阳明经脉,使之活血。血液流通,所以脸上的红晕消失。
对这样一个典型病例,朱丹溪在旁边仔细观察,认真琢磨,从找穴位到进针,边问边揣摩,逐步学到了针灸的知识。
朱丹溪一生著作甚多,有《丹溪心法》、《本草衍义遗》和《外科精要发挥》等近十种,其中《格致余论》、《局方发挥》为其代表作。
朱丹溪的学说,后世有褒和贬,但以褒为主。如明代医家方广说:“求其可以为万世法者,张长沙外感,李东垣内伤,刘河间热证,朱丹溪杂病,数者而已。然而丹溪实又贯通乎诸君子,尤号集医道之大成者也”(《丹溪心法附余》序)。但由于朱丹溪只明一义,过分强调了“阳有余”的一面,而不谈阳也有亏损的一面;在临床上太强调“滋阴降火”,因此,未免有它的片面性,从而遭到后人的激烈反对。张介宾也因其执着一端而攻之不遗余力,说:“丹溪之言火多者,谓热药能杀人。而余察其为寒多者,则但见寒药之杀人耳”(《景岳全书》)。历代对朱丹溪的学说评价,尽管有褒有贬,但总的来说,朱丹溪的学说在国内外仍有很大影响,在祖国医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面。日本医家曾成立“丹溪学社”,专门研究丹溪的学说。 纵观朱丹溪一生,有苦有泪,尤其是当他立在风雨中,乞求罗知悌收他为徒,教他习医时的情景,我们不难想象出他的毅力,为了一个目的,即使千折百转,不达目的仍誓不罢休。就是到了今天,这种精神仍值得我们学习。所以说,他不仅在医学方面,就是在做事方面,思想方面,也为我们积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,不愧为一代名医,一代名人。